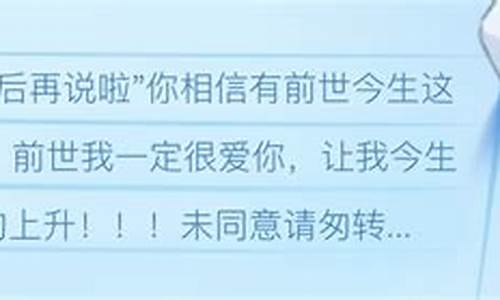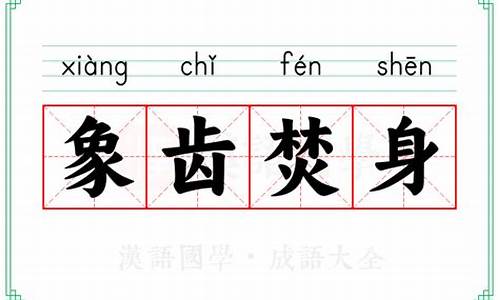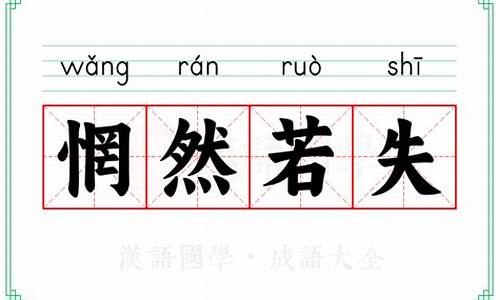说东道西又话北打一省份名-说东道西打一个数字
1.秦国在打六国时共发生过哪几次有名的战争?详细经过如何?
2.上海市里的各地区省份的名字由来?
秦国在打六国时共发生过哪几次有名的战争?详细经过如何?

百越之战
在大秦帝国军消灭了东方六国后,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把统一的目光放到了南边的百越之地,发动了对百越的战争,百越之地一般意义上也叫岭南,就是现在的广东和广西。在秦与百越的战争中,总共发生了三次,第一次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命令屠睢率领五十万大军南下攻击百越;第二次是公元前214年秦军在任嚣和赵佗的率领下攻击百越之战,该战平定了百越之地,统一岭南,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第三次是公元前210年,秦将赵佗攻瓯骆之战,历史学家一般称这次是第二战争的延续而已。总之这三次统称为“秦始皇三征岭南”。这三次发生的秦军和两广土著军的战争,本文重点介绍其中最重要和最惨烈的第一次战争。
第一次秦与百越的战争,在历史上也叫“秦瓯战争”,但是在史书上记载比较少,只有《淮南子》等少数书籍中有少量相关记载,这主要的原因我想主要是秦将赵佗在公元前214年攻占百越后不久就与秦朝廷貌合神离,在秦末又拒绝派自己手下的秦军部队北上与反秦起义军作战,封锁了两广与中原的联系,并在秦灭亡后建立起了南越国,按照现在的说法南越国属于地方割据政权,现今历史学家对地方政权的历史了解历来都不是很多,所以也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对这次战争的了解仅仅局限在少量史书的记载上。但是我们就从这不多的史料上也可以看出,这同样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战争,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秦军统一中国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当惊人的。
历史上之所以也叫此次战争为“秦瓯战争”,主要由于百越土著部队的最初首领是西瓯国首领译吁宋(西瓯国的位置在现在的广西),其实参战的百越军不仅仅是西瓯国军队,其他百越地区的越人其他土著武装也参加了战争,但是总指挥是西瓯国首领译吁宋、而主力是西瓯军而已,“译吁宋”这个名字很多历史学者都认为是百越土著军首领的名字,但是也有不同看法,说“译吁宋”这三个字很可能是百越军总指挥官在战场上喊的口令,因为“译吁宋”这个三个字和现在两广的壮语和粤语的“一二三”都很相似,秦军是外来人,这次战争秦军并没有深入两广腹地,对西瓯军的底细应该也了解不多,所以有可能把百越土著军的指挥官在战场上喊的口号当作该指挥官的名字了。但是可以确定该战争的百越军首领确实为西瓯国首领,至于该首领是不是叫译吁宋?如果不是的话,那战争中西瓯国首领的名字叫什么?为什么西瓯军在战场上喊“一二三”?这些都已经无法考证。
在历史上一般都把秦军的对手称为西瓯军,但下文为了顾及到当时广东和广西境内的其他越族士兵,所以以下把秦军的对手统称为“百越军”,其实主要是西瓯国军队。(如果按照现在的地理位置来看,则主要是广西的军队与秦军作战。)
秦军在这次战争中的参战兵力以及组成,在几乎所有的史书中都说到秦军调动50万大军在屠睢的率领下进攻百越,在《淮南子·人间训》中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但是这里也有疑问,五路秦军是同时进攻的吗?在广东和广西的地方志中记载,秦军在开始时期是屠睢一路和赵佗一路这两路一共20万人马最先发动进攻。但是那剩下的30万人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加入战争的呢?从史书上看,剩下的30万人应该在前线部队陷入战争泥潭,也就是在屠睢写部队缺粮的战报给秦始皇以前就出动了,因为在屠睢写的信中说到了自己的“五十万大军已经伤亡甚重”,而且根据考证,其中一路秦军开始攻击的是东瓯闽越地区(主要在现在福建),这路秦军也是五路中最晚才加入两广战场的一路。秦军这50万大军到底是那里的兵为主呢?根据我们湖南等地的地方志记载,秦军这次战争所动用的部队还是以以前灭楚国的部队为主力,但是为了适应南方作战,秦军这50万大军中也有不少于10万人的原楚国部队。
百越军在这次战争中的参战兵力则几乎没有任何史书有比较确切的记载,只能从部分考古资料中看出百越军的人数要远远少于秦军,而且当时的岭南百越基本上为蛮荒之地,交通不便,原始森林密布,自然环境恶劣,所以当时的两广总人口数根据考古学家的估计都不会超过50万,当时能战的适龄青壮年大致在5万人上下,这在不少野史中也有类似“百越土著军人数仅及秦军十分之一”的说法。但是不管怎么样,秦军的兵力是占绝对优势的,秦军为了这次战争的胜利是不惜代价的。
关于战争的经过,秦军五十万大军虽然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在装备上更是要远远超过百越部落军队,但是战争的过程却令秦军感到了战前从未想到的艰苦和压力,在战前,秦军考虑到了粮草可能会出现问题,也考虑到了南方炎热的气候对于大部分出生在北方的秦军士兵的不适应;但是秦军到了两广后才发现,战场环境的恶劣以及敌军的超乎寻常的凶悍顽强都是以前始料未及的,在史书上记载了以西瓯军为主力的百越军队的顽强抵抗,百越军在首领“译吁宋”的率领下与秦军进行了惨烈的激战,秦朝大军步步艰难,节节受挫,损兵折将,迟迟不能进入越人的世居领地,在战争中,百越军在首领“译吁宋”战后又马上另选了新的首领,并全线退入山地丛林中与秦军继续作战,百越军甚至不惜与野兽为伍,至不投降秦军,并且不断对秦军部队进行偷袭,切断秦军粮道,迫使秦将屠睢写信给秦始皇上报说秦军粮草已经不足,秦始皇被迫命令征调大量民工开凿灵渠,沟通了湘江和漓江水系,确保了秦军的粮草运输。另外秦军还有一个最大的敌人---------炎热的气候,秦军士兵多为北方人,大部分都为现在陕西、山西、河南等地人,不适应南方炎热的气候,士兵中瘟疫横行,直接影响了秦军的战斗力。以西瓯军为主力的百越军这时在新首领桀骏的率领下大致在公元前218年左右的时期对秦军发起了反击,秦军大败,根据《淮南子》记载,秦兵“伏尸流血数十万”,而秦军总指挥官屠睢也在现在的广西桂林一带被一支百越军夜袭部队击毙,迫使秦军“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惶恐不可终日,以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双方一直处于相持对抗的局面。而根据学术界讨论,秦军的阵亡在30万人上下,剩下的20万人全部退到两广的北部边界一带,但是百越军的伤亡同样十分惨重,也没有力量继续发动进攻,双方形成了对峙局面,而且一对峙就是3、4年时间。
一直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在灵渠粮道全面开通且粮草充足之后,征集“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为兵”(大概是商人和囚犯等人)近10万加上原先剩下的20万秦军部队,秦军再次集中了30万大军向百越军发动了最后的总攻,这时的百越军,根据不少野史记载,仅仅只有数千人而已,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此前的反攻作战和3、4年的武装对峙中,百越那区区几万人马早就被耗尽了,最后秦军几乎未遇到大的抵抗就占领了全部岭南,并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等三郡,这已经算是第二次秦攻岭南的战争了。
秦瓯战争狭义上说是秦王朝与盘踞在广西的西瓯国的战争,但是实际上应该说是秦王朝与整个南方百越民族的战争,这次战争完善了中华的基本版图,从此以后,广西和广东成为了中华版图的省份,期间虽然在秦末汉初时期曾经由秦将赵佗建立了南越国而独立出去,南越军在汉初高祖和吕后当政时期也曾经数次击败汉军的进攻,但是南越军同样消耗很大,在汉文帝时期,南越国撤帝号,与汉朝修好,在汉武帝时期,10万汉军南下进攻南越国,南越国经过此前的对汉战争,伤亡已经很大,无力抵抗强大的汉军,最后南越王率领南越全国在籍的40多万老百姓投降汉朝,此后两广之地再也没有和中华大地分开。
但是战争毕竟是残酷的,且不说秦军在三次战争中前后了损失了30多万人马,两广地区的老百姓也遭到惨重的损失,在历史资料中记载秦军在第二次战争后的部队全部留在两广,这些秦人与当地人融合,成为了现在的两广老百姓祖先的一支。这留下的近30万秦军士兵为两广的开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但是根据历史学家考证,在秦末农民战争、楚汉战争期间,两广并不是战场,此时的两广几乎已经算是独立出秦王朝,但是在《中国各朝人口》一书中却记载着在秦末战争刚结束的时候,两广人口只有40多万人,这里如果扣除那些留下的近30万秦军士兵,也就是说这时两广的原百越民族从秦瓯战争前的50万锐减到10万人这样,而这期间两广并没有什么瘟疫流行的文献资料,当然也不排除秦人在战争结束后还是不适应南方的气候从而造成水土不服而人口下降,但我认为战争造成人口减少的原因应该是最主要的,在战争中,起码有近40万百越人或或逃亡到东南亚。一直到汉武帝时期,已经在两广建立的南越国虽然说在建国初期有号称“百万带甲”,但是根据历史学家分析,南越国总人口最多的时候(大致是汉高祖以后的吕后当政时期)也不会超过80万人,士兵最多也就在10万人左右,“百万带甲”系为夸张而显示国威的说法,在最后投降汉朝的时候,南越人口在册投降的只有40多万人,如果算上那些不在册记录内的人口估计也不会超过60万人。
不管怎么样,这次战争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虽然民族的融合往往都要经过残酷的战争,但秦军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为两广的开发和建设奠定了基础。
上海市里的各地区省份的名字由来?
这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对道路命名的一种方案为基础制定的,没有特别的指向,主要道路多采用主要的省市名。
这些路名,解放后变动也不大。
解放后,新政权要对上海的路名要进行改置,后来的大量全国地名路名就是这样出现了,当然也保留了一些原有的路名.--如中华路就是原有的路名.
一般而言,上海道路的地名是与全国的省份的各大体方位大致相同,如我国的东北省份在东北方向,反映在上海的地名上也在上海的东北方向。松花江路,鞍山路等,在杨浦区--在上海的东北区。
还有上海地名的命名规则是,纵向(南北走向)是省的名称,横向(东西走向)则是省以下的市、地区、县的名称,如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延安路等是横向;而四川路,江西路,河南路,福建路,浙江路,贵州路,广西路,西藏路等--纵向。当然也有特例,如广东路它是省名的路,但它却是横向。
这规则在后来的运用上,基本上是这样的,可能特例会比较多。如成都路它是纵向的,但按规则它应该用在横向的路名上。
上海:路名解读城市
□本报驻沪记者沈颖摄影李江松
“私人记忆档案”
一个熟悉的地名往往构成记忆的大海,而地名像珊瑚礁保存一个错综的秘密,在人和地名之间有一份默契。
有些说来还不无讽刺。周泽雄在他的上海回忆录里写道:“然我的初恋得以在花溪路展开算得一个好兆头,但正是在凯旋路,我陷入了爱情的滑铁卢。还有一次,当我自以为已经优哉游哉地把爱情从武宁路牵扯到富民路,继而又从市中心的襄阳公园大踏步地拓展到僻远的临江公园时,在一条大名叫‘团结’的路上,我和她又差点鸡飞蛋打。”
地名是有其象征意味的,但这份意味不可能得到人民币那样的共同流通和集体接受,亦即不可能是字面上的那种,它属于你,而你或许又无从向他人道及。
仇女士家在四川路边的一座小洋房,虽然是与六户人家合住。毕业于著名的复兴中学,在四川北路顶端。这条路上的每一寸沥青和水泥都见证了她20岁以前的青春,用她的话说:“这条街上每一爿店铺里面的每一个柜台卖什么,我都知道。”
但是她的领地发生了巨大变化。每一次仇女士回娘家到四川路来转转,都会发现变化的东西。说到这里时她的眼角不住向上翘动,仿佛是一个王后在说后花园里,那个粗心的园丁没有按照她的意思修剪,结果“弄得一塌糊涂”。
她曾经是这条路当之无愧的主人,至少是主人之一。而她的丈夫周先生则不是。他出生于四川路不远的海拉尔路。两条路之间还有一条路,名叫四平路。在人口密集的虹口区,四平路一度是一个分界,它的东面是海拉尔路等地的棚户区,以苏北人为主,以西是四川北路、欧阳路等广东人的后裔。在1949年以后上海相对封闭的日子里,四平路两侧是两个街区,也是两个阶级,周先生为了打通这两个街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过年前周先生回到海拉尔路,看到自己爱之恨之的棚户区已经被推倒。这里成了新的住宅小区,均价达到7000元一平米。他说他感觉“一下子被呛住了”,只能把车停好悠悠地抽了很长时间的烟。
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关于地名的私人档案袋,各种地名都已被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分别归档。
敲入城市的历史密码
而对于一座城市,地名就像一套密码,你只有了解这座城市的全部底蕴,才有可能一一破译。
上海的城区不断扩大的过程,就是路名规律变化的过程。最早的上海城区局限于现在黄浦区南部还被称为南市(以前这里是单独的南市区)的一个部分。聚集了一批“尚文路”、“蓬路”、“望云路”等一批并不规整的路名和以当地大姓为命名的很多弄堂,“翁家弄”、“吴家弄”等。也许当年的上海太小了,人口也不多,路名混杂不至于让人迷路。
随着上海的变化,马路在被拓宽、延长和对接,这些路名也正在逐渐消失。但这个地区作为上海核心的时间是最长的,有好几百年———对于年轻的上海来说,这个数字和史前已经没什么区别了。
1840年以后,南市北面的一条小河“洋泾浜”开始引人注目,这条普通的小河成了英租界南缘的界河,同时也成了两种社会制度的界河,“东方”和“西方”的界河。其两岸也成了标准的华洋混居地,于是一系列不中不洋的词汇被冠名为“洋泾浜英语”。
由于迅速膨胀的人口,租界之间的频繁往来,滨河被填平造路。取何路名,一番争论,最后成了以英王命名、以法文拼写的中国大马路:爱丽诗路。上海解放后更名延安路,革命圣地之路。改革开放之后,这里又建高架路,延安路高架桥。由一条河,变成一条马路,又变成一条空中通衢大道,这不仅是一条路的历史,而且是映照着城市成长的城市发展史。
“一直到今天,要是只用一个词汇来概括上海,‘洋泾浜’可能还是最合适的称谓,虽然这条小河已经不复存在近一个世纪了。”研究上海历史的老先生说。
上海若没有淮海路,上海人将失却很多精致和布尔乔亚式的生活热情,这条最初由法国人筹划的大街,最早在1901年时叫“宝昌路”,宝昌本是法租界公董局的一位董事,一位“爱法国,也爱中国”的法国佬。他在法租界连续当了17年公董局董事,管理法租界的市政建设。1914年改为霞飞路。早在1885年,这个年轻的法国工兵士官乘船到上海游玩,除了法国的孩子们对其颇感兴趣以外,无人理会。但当欧洲大战爆发,霞飞在战场上屡建功劳,荣升法国东路军总司令后,法租界公董局的先生们立即想起这位霞飞将军曾经来过上海,尤其是玛纳之战,霞飞力挽狂澜,拯救了法国的危亡,法租界董事局的官员们欣喜若狂,立即决定从1914年开始将上海最繁盛的宝昌路改名为“霞飞路”。“霞飞路”叫了35年,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为纪念中国人民中著名的三大战役之一——淮海战役的胜利,这条路改为淮海路。租界全部收回,霞飞路才改名为淮海中路。淮海路全长约6公里,现分为淮海东路、淮海中路、淮海西路。
这是一条繁华而又高雅的大街,一条堪与巴黎的香榭丽舍、纽约的第五大道、东京的银座、新加坡的乌节路媲美的大街。尤其在行人稀少的晚上,读过几部法国小说的姑娘会自我感觉特好地把高跟鞋踩得跪响。
江湾五角场,它在国民政府时期一度倒是有希望成为上海的政治中心,所有东西走向的路都是以“政”字开头:政通路、政立路、政民路等等,而所有南北向的路都以“国”字开头:国定路、国和路、国顺路等等。还有一条小路的名字竟叫“国庠路”,这个“庠”字被用作路的名称,怕是全国鲜见。
结果,1949年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成为上海的西伯利亚,在疏离中感受流放。
以路的名义生长
随着上海城市的不断发展,市区面积扩大速度惊人。路名需求更加丰富,相应的规则就只能以一个大概的原则而行。这个原则就是尽量以国内的地名为路名,而且被命名的地区在全国的位置应该大致相当于这条路在上海的位置,同时不影响原有的主要道路。这也许是一种表达举国融融、四海一家的方式,并附带削弱上海人的本位意识。只是,在这份表达欲过于强烈时,地名应有的地域色彩也会剥离。东西向马路以城市命名,南北向马路以省份命名,遂使得南京路、延安路或福建路、山东路云云,不见得比纽约第五大街或第十六大街更具个性。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上海市区边缘出现了地区路名集群这样一个有趣状况,同省的地名在地图上被集中在一起。西南角上出现“钦州路”、“柳州路”等(分别都是广西地名),东北角则出现“鞍山路”、“双阳路”(东北地名),正北方则有“呼玛路”、“呼兰路”(黑龙江地名)。
事实上这一规则在上海沿用时间很长,但是随着城区范围的扩大该规律一直在起作用,同时新的命名又要考虑到不影响原有路名,因此有些地区在地图上离得很近,而在上海又离得很远,出现了多个东北集群等有趣状况。最典型的就是虹口区的赤峰路、多伦路等原上海市区的东北角,现在基本处于应该叫“上海路”或者“连云港路”的位置,非常有趣。
有安徽的好事者以此为据向上海市图书馆提问:为什么在上海没有一条安徽路呢?振振有词的。
这个问题让上海图书馆的同志有些为难,我的主观臆测是,在有可能命名“安徽路”的地方,一直没有出现一条需要命名的马路。要知道考证为什么没有“安徽路”,比考证为什么有条路叫“安徽路”更难。
实际上,起名字总是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没有哪条马路是生来就一定要叫某个名字不可的,而用来命名马路的省名,也不是只缺了安徽一个。
浦东开发后最受益的当属陆家嘴一带(陆家嘴相传为三国时东吴大将陆逊的原籍所在),一些并不出名,经济也不很发达的山东地名成了上海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比如博山、乳山等。
1990年代以后的发展突然让人们发现路名原来可以是一种无形财富。上海市地名办的负责人说,上海本没有宁夏路,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动申请命名的,宁夏的广夏集团、宁夏枸杞等著名品牌企业和特色产品也就顺理成章的进驻了宁夏路,为在上海市场大展手脚打开突破口。
在云南开远市的要求下,又有了开远路。市地名办的人士说,现在一套崭新的路名命名办法正在实施之中。一些路名开始披上炫目的时代色彩:如世纪大道、五洲大道等;而张江高科技园区出现了一批李时珍路、牛顿路等科学家的纪念路,似乎标志着这个地区的高科技含量。
路名无言,却几乎是我们政治、社会生活演变过程的显示卡。而任何一项试图穷尽地名意味的努力,也就难免成为美丽的愚蠢。
地名标识出一个个个体生命或城市生命的车站,不管我们曾作过逗留还是呼啸而过,我们都已进入了它珊瑚礁般的缠结之中。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